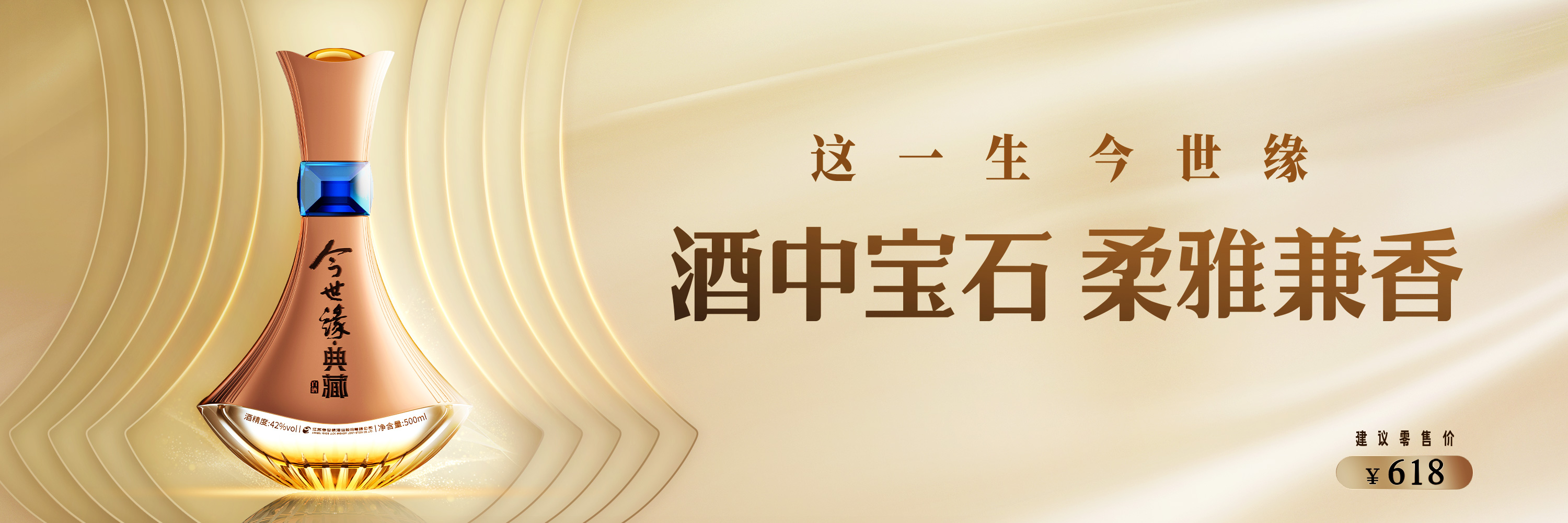今世缘·同题共写父亲母亲 | 父母是庄稼地里的两棵玉米
2025-07-08
墙上的挂钟走得磕磕绊绊,像极了父亲推着手推车碾过青石板的声响。这并不规律的滴答声,伴随着时光前行,而我,在光阴的辗转里,努力探寻父母爱情的模样。
犹记孩童时,对什么都充满好奇,总爱翻出母亲的陪嫁樟木箱,箱盖刚一打开,樟木味混着霉斑气息扑面而来。箱底压着褪色的红盖头,那红,已不再鲜艳夺目,边缘缠着半截水泥钉。母亲说,那是父亲当年盖房时随手掰断的,在她心里,这钉子比金戒指还牢靠。看着这奇特的组合,我仿佛看到父母爱情最初的模样,质朴且坚韧,如同这历经岁月仍紧紧相依的红盖头与水泥钉。
母亲常念叨:和父亲的故事,是从父亲帮她扛犁头开始的。可儿时,那些关于她和父亲相识相知的过往,在我耳中不过是寻常故事。直到某天,我再次偷翻她的陪嫁箱,发现褪色的作业本里夹着父亲长途寄来的信笺。1995年的秋夜,他在信笺背面写着:“今天搬砖时想,等攒够钱,给媳妇翻盖老房子。”字迹被水洇过,像落在宣纸上的淡墨。那一刻,我才明白,父母的爱情,就藏在这些看似平凡却饱含深情的物件与文字里。
1958年出生的父亲,赶上自然灾害,三岁便没了爹,是奶奶在大集体喂猪挣工分把父亲抚养成人。苦难生活的重压,也造就了父亲勇往无畏的性格,在以劳动力为主的当时,他成了十里八乡的庄稼好手。古语道: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,而给我父母牵线的是那不起眼的犁头。农忙时节瘦弱的母亲扛着比她高半截的犁头,吃力地走在乡间田埂上。父亲见状,殷勤地小跑过去帮母亲接过沉重的犁头,母亲报以感激的微笑。那一刻,两个年轻人眼神里的火花悄然绽放。自此,田间地头多了他们并肩劳作的身影,傍晚村口的黄葛树下,有了他们低声细语的甜蜜。他们交谈村里的小变化,说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,两颗年轻的心越靠越近。母亲相中了父亲的踏实勤劳,父亲相中了母亲的温柔贤淑,命运的红线将他们紧紧缠绕。
那时,没有华丽的婚纱,简单操办几桌酒席,亲朋好友的声声祝福,便是他们爱情最好的见证。婚后一年有余,我呱呱坠地,家庭生活压力陡增,家里经济捉襟见肘。伴随90年代北上南下打工潮的春风吹起山村,父亲也活泛起外出挣钱的心思。1995年初,父亲裹着露出棉絮的棉袄挤上绿皮火车,决定独自去投奔北京城的同乡建筑包工头寻找更多挣钱机会。一辈子我都记得母亲追着绿皮车厢小跑,把新买的解放胶鞋从窗口塞进去,喊着:“那边天寒,到了北京记得换鞋!”车窗泛起的雾气渐渐模糊了父亲的脸,我看见他别过身去,肩膀却在剧烈抖动。
父亲凭借不怕苦、肯干的劲头,在老乡承包的建筑工地站稳了脚跟。母亲则留在老家,一个人料理全家的农村自留地,照顾一家的吃穿用度。父亲会用为数不多的苦力钱,从遥远的北京给母亲打来座机电话,心疼地问询家里农活母亲是否适应,母亲也嘱托父亲在外面照顾好自己,家长里短的寒暄,直到电话响起嘟嘟嘟的挂机声。
父母逐渐有了一些积蓄,他们决定在老家开一家小小的早餐店。天还未亮,父亲就赶到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,母亲则在家里准备各种馅料、发面。凌晨三点,蒸包炉突然熄火。父亲蹲在油腻的地面上敲敲打打,火星溅在他开裂的手背上。母亲把我裹在围裙里,用嘴呵着冻僵的面团,呵出的白雾里混着铁锈味。她忽然笑起来:“你爸当年修茅草屋漏雨,也是这般模样。”在无数个日夜的辛勤付出下,早餐店的生意越来越好,从最初的几个顾客,到后来每天门庭若市。他们用自己的双手,为这个家撑起了一片天,也为我创造了一个逐渐走向小康的生活环境。“读大专时室友问我理想中的爱情是什么?我下意识想起父亲藏在糖盒里的止痛药,受伤了的父亲总说不疼,直到有天我看见母亲偷偷把药片磨成粉,拌在递给我父亲的蜂糖水里。原来最好的情话,是把苦嚼碎了,酿成不声不响的甜。
犹记得母亲农忙外出摔伤脚踝骨送医,父亲心急如焚,为母亲擦身、喂饭,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。母亲麻药散去醒来后,父亲轻轻握住母亲的手:“傻丫头,你要是不好起来,我可怎么办?”我在病房外看见父亲握着母亲的手,久久不松开,阳光从窗棂漏进来,在他们交叠的手上织出光斑。
母亲常说,她和父亲是“庄稼地里的两棵玉米”,根须缠在一起,风来的时候,一棵替另一棵挡沙,雨来的时候,另一棵替旁的那棵弯腰。
我的父亲母亲,是无数平凡夫妻的缩影。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誓言,却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和付出,书写了一曲扣人心弦的赞歌。他们的爱情如同一束温暖的光,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,我也学会用父亲笨拙的浪漫去爱,用母亲的隐忍温柔去经营生活。愿天下所有的父母,都能像我的父亲母亲一样,相濡以沫,白头偕老。
文丨郑元